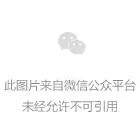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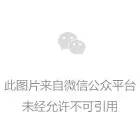
琺瑯 | ?琺瑯藝術出現(xiàn)在東方文明中有數(shù)千年之久,于唐宋時期傳入中國,在明清時期發(fā)展至鼎盛,因其繁復的工藝與嚴苛的用料標準,傳世的琺瑯作品中大多帶有宮廷、皇室的印記。其中以銅胎掐絲琺瑯最能將琺瑯釉料與金屬質(zhì)感融合,無限拓展琺瑯藝術的創(chuàng)作空間。掐絲琺瑯即人們熟悉的“景泰藍”,用銅制胎,通過手工掐制與圖稿上相同紋樣的銅絲為圖案,經(jīng)過與胎體黏接與多次點琺瑯釉料后高溫燒制、打磨而成。
提到琺瑯,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我國著名的工藝品——景泰藍。這種擁有千年歷史的工藝技術,在明代景泰年間制作達到了巔峰。但從明代至民國,景泰藍一直是奢侈的工藝品,發(fā)展到近代有點式微,成為偶爾的點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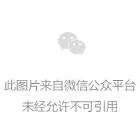
80后青年工藝美術家施君卻劍走偏鋒,選擇用琺瑯演繹當代藝術,他連續(xù)四年為F1中國大獎賽設計冠軍獎杯;受英國國會之托,為女王登基60周年慶典制作御座;與知名文化學者馬未都先生共同構思設計,為上海中心完成了480平方米的琺瑯藝術地面,獲得吉尼斯世界紀錄;以古書《山海經(jīng)》為靈感來源,創(chuàng)作了上海藝術博覽會20周年主題雕塑群……
?
施君從小就在充滿工藝與傳統(tǒng)的氛圍中成長,父親是上海工藝美術大師施森彬。還記得中學時一次,父親帶著他去外灘,指著那些外資銀行氣派非凡的銅門告訴他,這些都是出自自己之手。
那時施君第一次認識到,原來工藝美術也可以高大上,與人們的生活產(chǎn)生親密的聯(lián)系。他一直都很感恩這份幸運,能比同齡人更早地發(fā)現(xiàn)工藝美術的魅力,以及其在當代藝術中無限可能。
在英國留學時期,施君接觸到了不同國家風格的琺瑯藝術,作為在上海弄堂里長大的一代,他感知到了上海海派文化的沉淀給到年輕一代的機遇,于是選擇琺瑯作為媒介,去實現(xiàn)他心目中的海派文化傳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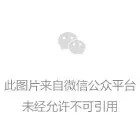
以此契機,他設計了第一把琺瑯椅,靈感來源于中國水墨畫,并在此過程中與團隊突破了大型琺瑯的燒制技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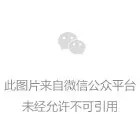
雖然施君謙虛地稱,當時無論是設計還是制作,都尚處在摸索階段,但這把琺瑯椅在現(xiàn)在看來依舊優(yōu)雅靈動。金色銅絲映襯著神秘熱烈的黑色,如深邃的宇宙對萬物生命的包容,仿佛有生命一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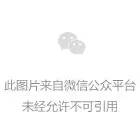
在琺瑯的諸多顏色中,只有純黑色琺瑯會用到900到1200度的大明火。如果你看見無瑕的黑色琺瑯,那就意味包含著頂尖的工藝。他還記得在這把琺瑯椅的打磨階段,現(xiàn)場水光飛濺,一位前來參觀的中東客人一眼相中,當場報出十幾萬的高價想要購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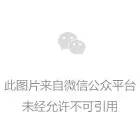
也是這次嘗試,冥冥中讓施君找到了一條琺瑯與家居相結合的道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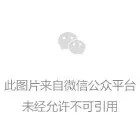 ?
?
2012年,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慶典,英國國會希望能訂制一把獨一無二的御座。他們被施君的創(chuàng)意打動,熱情地向這位上海設計師拋出橄欖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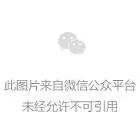
▲
這把海藍色銅胎掐絲琺瑯座椅現(xiàn)已被白金漢宮永久珍藏,當時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去設計、制作。
萬瓣手工銅花,上萬次填釉上色,搭配寶石美玉、純金鎏金,結合歐式布藝軟墊,經(jīng)50道復雜工序,反復焙燒、淬煉。座首、扶手位置選用大范圍鏨刻花紋并鎏金花紋圖案,局部點綴美玉。富有層次感、流暢的線條紋飾體現(xiàn)了皇室的尊貴、皇家氣度與威儀。
▲
“女王御座”一共制作了兩把,除交付給英國王室的座椅,另一把如今專供陳列展示。普通人也可以訂購,售價為20萬英鎊,購買者必須向王室提出申請,經(jīng)由身份核查,通過后才能購買。
這以后施君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,創(chuàng)立品牌,結合傳統(tǒng)工藝與當代設計,為琺瑯工藝注入活力。他與團隊,就像一條漂洋在琺瑯藝術藍海中不斷探索的大魚,安全的島嶼基本不去,永遠在探索新的大陸。
他將目標瞄準大型作品創(chuàng)作,把以毫米計量的琺瑯藝術發(fā)展到以米為單位的法瑯彩雕塑,類似的巨型琺瑯作品,全世界只有他能完成。
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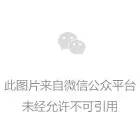
▲
為山東興隆文化園造建的釋迦牟尼佛像18米高,是世界最大的琺瑯立體雕塑,創(chuàng)下吉尼斯世界紀錄。
▲
上海中心大廈37層480平方米的大型琺瑯藝術地板“輪回”,由施君與中國著名學者馬未都先生等人共同構思設計,設計靈感源于三位藝術家對宇宙能量的理解以及「輪回」這一概念的詮釋。
▲
華山路688號是一棟富有人文情懷的豪宅,對面就是許多民國時期名流曾駐足的枕流公寓,這片總面積300平方米的琺瑯幕墻第一次將琺瑯運用在建筑外立面。
有意識弱化傳統(tǒng)的琺瑯紋飾色彩明麗繁復,在很多些作品中只用到深藍與銅胎本身的褐色兩種色彩。猶如中國水墨畫中的“墨色”與“留白”。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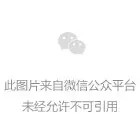
“在過去,生活里到處都是灰蒙蒙的,琺瑯滿足了人們對色彩的想象,但現(xiàn)在,時代像掉進了染缸里,琺瑯存在的意義也會發(fā)生改變。”
▲
《滄海》
隱藏在海水中的金色掐絲象征海洋孕育的無數(shù)鮮活的生命,中間兩只遨游的鯨魚是無數(shù)生命的代表。這組墻面裝置中最大的一件直徑2米,面積達4.37㎡,掐絲3785根,制作時需要專門定制大型燒窯,從而實現(xiàn)一體燒制,讓琺瑯達到最佳成色效果。

▲
《淼漫》
“水不在深,有龍則靈”蜿蜒激蕩的水流匯聚成似龍的抽象外形,帶給觀眾一種神秘體驗。
▲
《山海經(jīng)》系列
七件作品分別是《山海經(jīng)·飛魚》、《山海經(jīng)·胐胐》、《山海經(jīng)·鳴蛇》、《山海經(jīng)·化蛇》、《山海經(jīng)·犀渠》、《山海經(jīng)·?鳥》和《山海經(jīng)·夫諸》,意圖通過這一系列的作品表達人類從古至今對自然的敬畏之情。
正如施君引以為傲的海派文化,是多國文化與江南傳統(tǒng)交織的結果,用寫意化的東方哲學來表達琺瑯這種由西方傳入的“舶來品”,或許是他對琺瑯藝術在當下時代的理解。?
他希望融合東方與西方、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,創(chuàng)作出符合當下時代的理念、審美的作品,讓琺瑯制品重新返回生活。百年后再回看,這些琺瑯作品能成為一件古董。